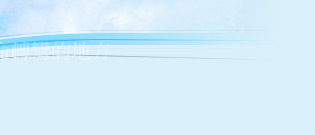一年後,當我寫完這些故事時,隨手拿起一本書,正好讀到加拿大作家瑪格莉特.愛特伍(Margaret
Atwood)在《與死者協商──談寫作》一書中談到她的寫作觀點。她引用聖經約伯記裡面的話形容作家是:
『只有我一個人脫逃,來給你報信。』
埋首在家裡寫《危險心靈》的結尾時,是二○○三年的四、五月間。那時我已經跟著書中那些十五歲的孩子一起活了將近一年。《危險心靈》結尾的書寫是很折磨人的過程。我不但吃不好,睡不好,甚至心悸、頭痛,全身腰、背到手指全都肌腱炎發作。比那更糟的恐怕是我的心情。
大約是那時候的某一天吧,我心浮氣躁地走上台北街頭。我本來也許只是想散散心的,可是我卻怵目觸心地發現滿街的人忽然都戴上了口罩。
我說忽然也許不精準,可是那樣的心情卻一點也不誇張。
那時候史無前例的SARS在台灣已經蔓延開一個多月了,相對於大家的焦慮,我似乎有點遲鈍了。可是我的確是那之後才開始打開電視、翻開報紙,這才接上了所有紛紛攘攘的一切。
我試著打電話給醫界的老朋友,探詢情況嚴重的程度。不確定的氣氛似乎感染著每一個人。那時傳說台北就要封城了,有個感染科醫師悲觀地告訴我:
『要是病毒繼續突變下去,早晚發展出潛伏期就能傳染的致病力,到時候台北的路旁恐怕見得到屍體堆積的景象……』
現在看起來,事情似乎清晰了很多。可是當時的感覺卻完全不同。我在小說荒謬的結尾裡掙扎著,一點也沒想到小說外面等著的,卻是另一個更荒謬的世界。
生活還是繼續著。冥冥之中,偶爾會想起,是不是我們都快死了?然而那只是靈光閃現。仍然上學的小孩,上班的太太,我也在一樣的書房裡,隨著《危險心靈》中十五歲的小男主角在龐大而失序的社會結構裡抗爭、吶喊,忍受分內的失眠、頭痛,全身酸痛。
那時朋友聚會,不知怎地聊起了一個很過時的話題,沒想到大家竟興緻昂然。題目是:假如明天是世界末日的話……
有個朋友毅然決然地表示:『我要去搶銀行。』
『你已經那麼有錢了?』我問:『搶了那麼多錢,什麼時候花?』
『花錢沒什麼了不起,我想搶錢,做些這一生從沒有作過的事情。』
另一個朋友說:『我想和家人在一起,做最後的一趟旅行。』
還有人浪漫地表示:『我想去跟曾經愛過的女人一一道別。』大家吐槽他:『恐怕是一一道歉才對。』
輪到我時,想不出什麼來,我像是抗議什麼似地說:『我還不能死。』
『為什麼?』朋友問。
我忽然脫口而出:『我的故事還沒有寫完。』
說完朋友全笑我工作狂。我也被自己脫口而出的話嚇了一跳。這算什麼答案呢?那天晚上我作了一場夢,夢裡是瘟疫末世的景象,人類一個接著一個死去,生物也逐漸滅絕,一個作家在搖搖欲墜的危險裡寫著,口中唸唸有辭:
『我還不能死。』
反正那是一個清醒的時候想起來就覺得很好笑的角色就對了。
後來我開始重讀薄伽丘的《十日談》。《十日談》講的是西元一三四八年流行在佛羅倫斯的黑死病。一群男女逃到郊外去避疫,因為太無聊了,彼此約定每天講一個故事和大家分享。
書中寫到瘟疫流行時描述著:
真的,到後來大家你迴避我,我迴避你;街坊鄰舍,誰都不管誰的事;親戚朋友幾乎斷絕了往來,即使難得說句話,也離得遠遠的。這還不算,這場瘟疫使得人心惶惶,竟至於哥哥捨棄弟弟,叔伯捨棄姪兒,姊妹捨棄兄弟,甚至妻子捨棄丈夫都是常有的事。最傷心,最教人難以置信的是,連父母都不肯看顧自己的子女……
佛羅倫斯的街道上的景象更是:
每天一到天亮,只見家家戶戶門口都堆滿了屍體。這些屍體又被放上屍架,抬了出去。要是弄不到屍架,就用木板來抬。一個屍架上常常戴著兩、三具屍體。夫妻倆,或父子倆,或者兩三個兄弟放在一個屍架上,成了一件很普通的事。人們常常可以看到兩個神父,拿著一個十字架走在前頭,腳夫們抬著三四個屍架在後面跟。常常會有這樣的事情發生,神父知道要替一個人舉行葬禮,卻忽然來了六七具屍體……
很特別的是,《十日談》裡面輪流講故事的人都帶著一派歡樂的氣氛,故事也全都荒誕不經,有貪婪的人、假正經的人,更多是荒謬的命運、愛慾情仇的故事……或許正因為明天是無常的吧,那些在不可知陰影底下的歡娛嬉鬧,深色絨布上的寶石似地,呈現出一種璀璨而無法言喻的生命質感,深深地吸引我。
現實生活裡,我持續在《危險心靈》小說的結尾裡掙扎著。截截上升的疑似感染、死亡數目仍占據了每天的傳播媒體。有時候,寫不下去了,暫時從小說的世界走出來透透氣。打開電視,又看到了喪禮,家屬的哭泣、哀嚎,殿堂的議員交相指責……
和《十日談》沒什麼兩樣的是,情況愈是吃緊,我們愈是『冒著生命危險』和朋友聚餐說笑,縱情歡樂。時間愈來愈多。有一回,杯盤狼藉,酒酣耳熱之後,幾個問題忽然浮上了我的腦海:
二00三年,就像一三四八年的佛羅倫斯一樣,我們都在台灣想些什麼?做些什麼?我們期待什麼,又害怕什麼?
這些心情,將來,甚至是當我們都死了之後,還有誰在乎嗎?
我沒有對任何人提起。生活本身已經夠麻煩了,更何況這些大概是任誰也無法回答的難題吧?
約莫兩個禮拜之後,我終於寫完《危險心靈》的結尾,把書稿交了出去。我心力交瘁,倒在床上呼呼大睡。我一共睡了一天一夜,這次一個夢也沒有了。
等我醒來,有股莫名的衝動又把我拉回電腦桌前。我拉出了鍵盤,開始打下了最初的幾個字:
這是一個朋友告訴我的故事……
我一邊寫,一邊想起那些對我說著故事形形色色的臉孔,以及各式各樣渴望聽故事的眼神。在那之前,我幾乎沒有想過我的下一本書會是什麼。可是寫著寫著,我忽然知道接下來該怎麼做了。
這一系列極短篇就是這樣開始的。
那已經是一年前的事了。儘管當時我一點也不確定接下來我會聽到什麼,或者往後這個世界會變成怎麼樣。
一年後,當我寫完這些故事時,隨手拿起一本書,正好讀到加拿大作家瑪格莉特.愛特伍(Margaret Atwood)在《與死者協商──談寫作》一書中談到她的寫作觀點。她引用聖經約伯記裡面的話形容作家是:
『只有我一個人脫逃,來給你報信。』
是那個時間點讓我訝異得不知從何說起。一年的時間不算長,那句話簡直像是早在那裡等候我似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