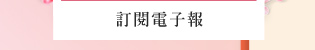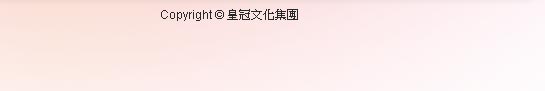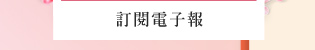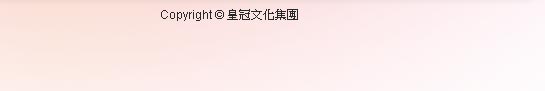愛過你
Chapter1 漂泊
生命中的某一天,有個人突然闖進來,而你覺得他很特別,
比你所遇到過的每一個人都要特別,會不會就是危險的開始?
1
誰能夠預見十五年後的事呢?比如說,一個從小在香港西區長大,讀書、工作都離不開西區的女孩,怎會想到十五年後的一個夜晚,她會在西非貧瘠小國寂寂的蒼穹下苦苦地想著心愛的人?想著他現在離她有多遠。時間再往前推移,多年以前,安徽蕪湖一座孤兒院裡那個只比她大兩歲的小男孩,甚至不知道五個小時之後能不能吃上一頓飽飯。
那是一九九九年,我的實習生涯正式開始,那年我二十二歲,初生之犢,滿懷期待又戰戰兢兢。實習醫生是醫生之中最低級的,負責所有的雜活,當我穿上白大褂走進病房,我以為等著我的是做不完的工作、看不完的病人、挨不完的罵,還有因為缺睡而變得遲鈍的大腦和連續熬夜的黑眼圈。多年以後,當我回望當天那個青澀的小醫生,我才發現,那時候等著我的還有此後人生裡漫長的歡聚和離別、希望和失望、成長與挫敗,而這一切都和程飛有關。
那一年的十二月,我剛剛結束了小兒科的實習,轉到內科。
內科一向被喻為戰場,人手永遠不夠,病人絡繹不絕,這樣一個兵荒馬亂的地方,卻也是每個實習醫生最好的訓練場。經過內科的洗禮,才算是在戰火中走過一回,可以準備好去打下一場仗了。
我和程飛相遇的那天,同學史立威家有喜事請假,求我幫他頂班。內科本來就只得我和史立威兩個實習醫生,我一個人做兩個人的工作,已經連續當班超過六十小時,整張臉因為缺水而冒油,一顆頭好像平時的兩倍大,連走路也會睡著。要是當時我在病房裡不小心摔一跤,我大概也會懶得爬起來,直接趴在地上睡去。
程飛見到的,是最糟糕的我。他後來說,那天看到我的時候,他確實被驚豔到了,可誰都聽得出他不是這個意思,他的原話是:
「還沒來香港之前,我一直以為香港的兩隻熊貓安安和佳佳……是叫安安和佳佳吧?是住在海洋公園裡的,沒想到西區醫院這裡也有一隻,還會幫人看病呢……我以後是不是可以叫妳熊貓?」
「不可以,太難聽了。」我板起臉說。
程飛沒理我的反對,自己揚起一邊眉毛偷笑,嘴角笑歪了,眼睛也皺了,而我竟然不生氣。從那以後,有段時間他都不叫我的名字方子瑤,偏偏要叫我「熊貓醫生」,我永遠記得他那個樣子,那麼可惡,一張嘴壞到透頂,卻又那麼天真和幽默。直到好多年後,發生了那麼多事情,每當想起這一幕,我還是會不禁微笑,還是會想念那天和那時候的我和他。
程飛初次見到我的時候,嚴重缺睡和腦部缺氧的我壓根兒沒看到他。六十小時不眠不休,那天我看誰都像一個幻影,朦朦朧朧的,就連我在徐繼之的病床邊做過些什麼,又對他們兩個說過些什麼,我也想不起來了。
「那天妳問我們兩個是不是一對兒。」程飛後來告訴我。
我完全不記得我有這麼說過。我怎麼可能說出這樣的話呢?我可是個很嚴肅的小醫生啊。
我更早之前就在病房和病房外面的走廊見過程飛幾次,在我的記憶中,那才是我們真正的初遇。或者那時候他也見過我,眼光卻不曾停留在我身上。我太普通了,他並沒有從一開始就注意我。
那時的他也比我好不了多少。我一直堅信我的黑眼圈、蒼白的臉色和時不時兩天不洗的頭,是神聖的,是為了病人犧牲小我,而程飛呢,他本質就是個流浪漢。那時我並不知道他的過去。
我和程飛的相遇,是因為另一個人。
***
徐繼之是十一月底住進20A內科病房的,他得了白血病,要做化療才有機會活下來。當時我剛剛轉到內科實習,他只比我大幾個月,和我上同一所大學,我是醫科畢業之後在醫院全職實習,完成這一年的實習,拿到醫生執照,才能成為正式的醫生,而他已在讀物理系研究院的第二年。這是他住院之後,我們兩個偶爾聊起來才知道的。
一開始會注意到他,是因為他那麼與眾不同。
化療的痛苦,即便是最強壯的人也受不了。劇烈的嘔吐、高燒和發冷輪番上場欺侮你,身上大大小小的瘀青、渾身的疼痛、破嘴唇和每天大把大把掉下來的頭髮,更是把一個原本健康的人折磨得毫無尊嚴。他卻總是那麼安靜,一雙脆弱而敏感的大眼睛始終帶著一抹明亮的微笑。
只要精神稍微好一點,他就會坐起來戴上厚厚的近視眼鏡入迷地看他那幾本泛黃捲邊的棋譜,又或者在病床的餐桌板上擺好棋盤跟自己對弈。這些圍棋棋譜全都是那個自封為一代棋俠的對手帶來給他的,這個對手說無敵是最寂寞,吩咐徐繼之不能在還沒有打敗他之前死去。
跟他聊起這些事的那天夜晚,病房挺安靜的,很多病人都睡了。我替他量體溫,他有點發燒,但精神還不錯,亮著床頭的小燈,擺好棋盤跟自己下棋。
「他這麼說只是想鼓勵我,其實我怎麼都贏不了他。」徐繼之說著挪了一顆黑子。
「也不一定的,只要活著就有機會。」我試著鼓舞他。
「我也可能活著但一直輸。」他喃喃說,然後問我,「妳會玩圍棋嗎?」
我搖搖頭:「你那個朋友真的有這麼厲害嗎?竟敢自稱一代棋俠。」
「總之是未嘗一敗,宿舍裡沒有一個人能贏他,我們這幾個人可都是玩圍棋玩了很多年的。」
「是不是就是常常來看你的那個人?頭髮像泡麵那個?」
「泡麵?」
「嗯,自然鬈,挺像泡麵的。」
徐繼之哈哈笑了一聲:
「沒錯,就是他,一直覺得他的髮型像某種能吃的東西,跟他做了快兩年的室友我都說不出來是什麼,啊,原來是泡麵!」
這天之前我還不知道他叫程飛。徐繼之住院的那陣子,他每天都會出現。那時的他皮膚曬得黑黑的,人長得又高又瘦,總是穿著破舊的牛仔褲、衛衣和西裝外套,背著個破爛的黑色尼龍背包走進病房。他有時會一直待到很晚,坐在床邊那張塑料椅子上陪著徐繼之聊天。他身上那件深藍色棉布西裝外套從來沒有換過,好像從高中時代就一直穿著,白天穿,夜晚穿,睡覺也穿,早就被他穿得走了樣。
雖然頂著個泡麵頭,全身縐巴巴的衣服近乎襤褸,牛仔褲也有點縮水,腳上一雙球鞋更是又破又髒,程飛身上卻沒有半點寒酸模樣,劍眉星目,臉帶微笑,走起路來昂首大步,一副自得其樂的樣子,完全不在乎別人的目光。
「又輸了。」徐繼之看著棋盤皺眉,「這局棋我們今天還沒下完。程飛太難捉摸了,每次一開局好像是他輸,可是到了中段他就一路殺回來,其實他一開始根本沒輸。他借給我看的棋譜,他十歲前就已經全部讀過。他就算一邊看小說一邊下棋也能贏我們,贏了我們的錢就統統拿出來請大家吃東西。他很喜歡吃白切雞,一個人能吃掉一隻,是個很有趣的傢伙。很少看到他溫書,或者去補習,他就是玩牌、泡吧、打籃球,女孩子都喜歡來找他玩,很瀟灑的一個人,我特別羨慕他。」
徐繼之摘下眼鏡,把護士留給他的一杯溫橙汁喝完,疲累地說道:
「要是我能夠活著離開這裡,我真的希望可以活成他那樣。」
聽到他這麼說,那時初出茅廬的我,突然希望自己老十歲,再老十歲,成為一個大醫生、一個好醫生,知道怎樣治好他的病,或者至少知道怎樣減輕他的痛苦。然而,那一刻,我只能賣弄我的小聰明,跟他說:
「你當然可以活著離開這裡。知道為什麼嗎?」
徐繼之怔怔地看著我,等著我告訴他。
我聳聳肩,一隻手放在病床的護欄上,微笑說道:「你竟然沒留意嗎?你這張病床是七號,沒什麼的,『七』剛好是我的幸運數字。」
「啊,那我太幸運了。」徐繼之咧開嘴笑了。
我點點頭,不知道這麼說是否給了他一點安慰。然而,當我轉身背向他緩緩走出那間安靜的病房時,我的眼睛早已經一片模糊。我記得那樣深刻,因為那是我頭一次為一個病人掉眼淚。
那時我沒想過,許多年後的一天,他再一次讓我掉下眼淚。
***
隔天傍晚,我又見到程飛。
晚上的探病時間還沒開始,來探病的人都得在病房外面的走廊上等著。我從病房出來,準備搭電梯到樓下,他剛好坐在一張電梯附近的長椅上,戴著一只耳機聽歌,一副悠然自得的樣子。兩個穿校服的十三、四歲的孩子坐在他身邊,看來像兩兄妹,正拿著作業本低著頭做數學題。
「女孩子要學好數學。」程飛對那個秀氣又苦惱的少女說。
「為什麼啊老師?」少女抬起頭茫然地問他,她看來一點都不喜歡數學。
「學好數學,將來嫁人容易些。」程飛挑眉說。
「那我不用學了,我是男生。」那個機靈的少年馬上說。
少年剛說完就被程飛打了一下頭:「信不信我把你小頭打成大頭?一個男人數學不好將來怎麼出來混?你沒聽過博弈論嗎?想要在酒吧裡追到最漂亮的那個女孩子,就要懂博弈論。」
正在等電梯的我,聽著偷偷笑了。
探病的鐘聲響起,病房的兩扇自動門緩緩打開,程飛站起來,摘掉耳機還給那少年,說:「你們先去吃飯,我進去看我朋友。」
「老師,要幫你買盒飯嗎?」
「你有錢嗎?」
「有啦。」那少年說。
「冰淇淋……」進病房之前,程飛回頭跟那少年說。
那少年回答:「記得啦老師,還是芒果冰淇淋對嗎?」
程飛擺擺手,表示對了。
少年和少女匆匆收起作業本,和我擠同一部電梯到樓下去。
我站在電梯最裡面,看著擠進來的那兩兄妹的背影,想起他們三個人剛剛的對話,想起程飛那一本正經的腔調,我噗哧一聲笑了,幸好我當時戴著口罩。
2
跟程飛正式見面是我替史立威頂班的第二天。傍晚時分,我頂著兩個黑眼圈走進20A內科病房,感覺好像已經有一個世紀沒有睡上一覺了。我白大褂一邊的口袋裡有一個黑色小筆記本,密密麻麻寫滿了當天要做的事,我把筆記本拿出來看了一遍就開始幹活。
當我走到徐繼之的床邊,程飛也在那兒,他剛剛替徐繼之上完課,回來講給他聽,一本寫滿了物理公式的筆記本攤放在餐桌板上,兩個人很認真地討論。以下的對話是程飛事後告訴我的。
「這是程飛,這是方子瑤。」徐繼之給我們互相介紹。
我瞇眼看了看他們兩個,然後說:「哦,你們兩個是一對嗎?」
說完,程飛和徐繼之兩個同時愣愣地張嘴看著我。
而我,據說我當時就像冷面笑匠一樣若無其事,從口袋裡拿出我的聽診器戴上,準備做檢查。
「然後我就問妳:『醫生,這個和他的病有關係嗎?』」程飛笑嘻嘻地說。
要不是他這麼說,那天的事我完全想不起來。他這麼一說,我又好像有點印象。幸好當時只有我們三個,沒有別的人聽到。
程飛告訴我這件事的時候,我們是在醫院的餐廳裡碰到。那天夜晚九點,餐廳差不多打烊了,我終於可以坐下來吃飯。他和前幾天那對小兄妹坐在另一桌,就在飯堂那棵瘦弱的綠色塑料聖誕樹旁邊。據說那棵聖誕樹每年的十二月都會擺出來,這麼多年來就沒有換過新的,年紀比我們這些實習醫生都要大。那兩兄妹在那棵掛著幾個彩球和小鈴鐺的老聖誕樹旁邊一邊吃飯一邊做習題,程飛看到我,衝我笑笑打招呼,走過來坐下,然後把那天的事說了一遍。
我當然不會承認,而且裝出一副我不記得我有這麼說過的表情。
「妳為什麼會認為我們是一對呢?就因為我們那麼好?男人和男人之間就不能有純友誼嗎?妳真是太俗氣了。」程飛兩條眉毛擰在一起,看我的神情分明是在捉弄我。
「你也很俗氣就是。」我看了他一眼。
「我哪裡俗氣?」
「為什麼說女孩子學好數學將來嫁人容易些?」
程飛恍然大悟:「妳聽到了?」
我不置可否。
「妳讀理科,數學應該也不錯吧?雖然沒有我好。這是很簡單的數學啊。愛情就是關於機率,說到機率,就是數學的事。」
「如果這裡機率的意思是緣分,那我同意。」
「緣分太虛無了,機率精準得多。先不講愛情,講嫁人這事吧,因為我說過數學好的女孩嫁人容易些。妳聽過數學有個『最佳停止理論』嗎?」
「沒聽過。」
「那妳就很大可能會孤獨終老。」
「你才孤獨終老。」我白了他一眼。
「不過,幸好妳遇到我,妳從今天開始就不會孤獨終老。」
我禁不住眨了眨眼睛,以後也常常想起他這句話。遇到他,就不會孤獨終老?他當時說得太興奮了,一心只想著表演他那個「最佳停止理論」,並沒有意識到這句話對一個女孩子來說還有另一重意思。
「『最佳停止理論』可以幫妳找到命中註定的那個人。」他說。
「真是聞所未聞,我洗耳恭聽。」我吃著我的叉燒飯,等著程飛發表他的偉論。
「這張紙可以借我用嗎?」他說著拿走我放在餐盤上的餐巾紙,用筆在上面寫下一條簡單的公式:
「P是妳找到最佳人選並且成功和他結婚的機率,這個機率其實是妳這輩子的潛在情人,即n,和被妳甩掉的情人的數目r 所構成的。如果妳這輩子註定和十個人交往,妳找到最佳人選的最佳時機是在妳甩掉前面四個情人之後,那時妳找到真命天子的機率是百分之三十九點八七;如果妳這輩子註定和二十個人交往……」他站起身,快步走到他原本坐的那一桌,把吃到一半的蛋炒飯和芒果冰淇淋拿過來,吃了一口飯,繼續說,「這樣的話,妳應該甩掉前八任情人。那麼,妳找到真命天子的機率是百分之三十八點四二。」
程飛咬著勺子,端詳了我一會兒,似笑非笑地說:「啊,假設妳這人特別風流,追妳的人比天上的星星更多,那妳應該拒絕前面百分之三十七的人,那麼,妳找到真命天子的機率就是三分之一!」
他揮動著手裡的筆,越說越激動:「如果妳不跟隨這個策略,而是迷信妳說的所謂的緣分,妳找到最佳人選的機率只有1/n,也就是說,如果妳跟二十個人交往,嫁給對的人的機率只有百分之五,但是……妳照著這個策略,機率就會提高到百分之三十八點四二。」
「我覺得你可以去開婚姻介紹所了。」我沒好氣地說。
「這個我倒是沒想過哦,基本上,我覺得婚姻是違反人性的,要是我去開個婚姻介紹所,不就等於去做一件沒人性的事嗎?這種事我做不出來。」
不知道為什麼,我當時笑了。
「你很詼諧……」
「這是讚美嗎?」他做了個鬼臉。
「我還沒說完呢,你沒發現你這套理論有一個很大的漏洞嗎?現實生活中真的有那麼多潛在情人排著隊讓你選嗎?你以為每個女孩都是瑪麗蓮.夢露或者伊麗莎白.泰勒嗎?」
「哦,妳說得對……」他點點頭,「這個策略還可以簡單化,而原則是一樣的,畢竟妳並不是瑪麗蓮.夢露。」
「啊……謝謝你提醒我。」我嘴角假笑了一下。
「我們忘記人數,用時間來玩吧,假設妳十五歲開始跟男孩子約會,希望四十歲的時候結婚……」
「四十歲?」那時的我覺得四十歲已經很老了。
程飛一口飯一口冰淇淋,慢條斯理地說:「只是假設,別怕。」
「我沒怕。」我不在乎地看了看他。
「假設妳希望四十歲的時候結婚,那麼,在妳交往時期的前百分之三十七,也就是妳滿二十四歲之前,應該先不要和這個時期的男朋友結婚,而是好好瞭解一下戀愛市場的運作,摸索一下自己想要個什麼樣的老公,等到淘汰階段結束,妳就可以選擇妳認為比所有前任都更好的那一個,這樣就可以大大提高妳找到最佳人選的機率。當然,這個策略也是有缺點的,但是也最切合現實生活的狀況,許多女孩子往往到了二十五歲,坐二望三的時候就想要安定下來了。」
我忍不住了,看了他一眼,然後說:「你是不是太沒人性了?難道一個人為了找到最佳人選就要甩掉前面幾個人嗎?二十四歲之後遇到的也不一定就比以前交往的男人好。」
他看著略微生氣的我,好像覺得這樣的我很有趣:「不是我沒人性,我們現在說的是機率啊,世間的一切都充滿模式,愛情也不例外,當然啦,數學只是一些原則,有些女孩子一輩子可能只得一個追求者,根本就沒有機會甩掉前面的百之三十七。」
說完,他哈哈大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