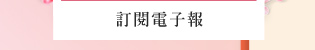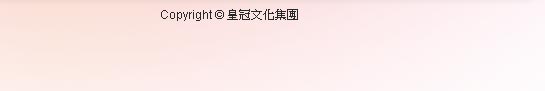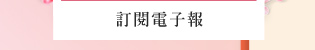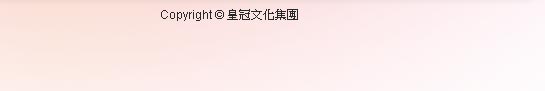三個A CUP的女人
我的第一個胸罩不是我自己的,是我母親的。一天,母親跟我說:「周蕊,你該戴胸罩了。」因為提不起勇氣自己去買胸罩,所以我偷偷拿了母親的胸罩戴在身上,那個胸罩是肉色的,兩個罩杯之間縫上一朵紅花。我自己擁有的第一個胸罩是向流動小販購買的,他是一個男人,用手推車推著胸罩在鬧市擺賣,數十個胸罩堆成一個個小山丘,場面很壯觀。
我現在是一個內衣零售集團位於中環總店的經理,這間店專門代理高級的法國和義大利名牌內衣。這段日子所遭遇的故事告訴我,女人的愛情和內衣原來是分不開的。
高級胸罩有一個哲學,就是越少布料越貴。布料少代表性感,性感而不低俗是一種藝術。一個女人,能夠令男人覺得她性感,而不覺得她低俗,便是成功。聰明女人懂得在性感方面投資,因此我們的貨品雖然貴,卻不愁沒有顧客。
我們主要的顧客是一批高收入的職業女性,那些有錢太太反而不捨得花錢,我見過一個有錢太太,她脫下來的那個胸罩,已經穿得發黃,連鋼圈都走了出來。女人嫁了,便很容易以為一切已成定局,不再注意內衣。內衣生意最大的敵人,不是經濟不景氣,而是婚姻。刺激內衣生意的,則是婚外情。
這天,差不多關店的時候,徐玉來找我,店外經過的男人紛紛向她行注目禮。她是意態撩人的三十六A。
「周蕊,你有沒有鉛筆?」徐玉問我。
「原子筆行不行?」我把原子筆遞給她。
「不行,要鉛筆。」徐玉說。
我在抽屜裡找到一支鉛筆,問她:「你要寫什麼?」
「我剛拍完一輯泳衣照,導演告訴我,拿一支鉛筆放在乳房下面,如果乳房低過鉛筆,便屬於下垂。」
我認識徐玉不知不覺已有三年,那時我在設計部工作,徐玉來應徵內衣試穿模特兒。她的身材出眾,身高五呎五吋,尺碼是三十六、二十四、三十六,皮膚白皙,雙腿修長,穿起各款內衣十分好看,我立即錄取了她。自此之後,我們時常「貼身」接觸,成為無所不談的朋友。我曾經精心設計了幾款胸罩,向我那位法國籍上司毛遂自薦,希望他把我的作品推薦給總公司,他拒絕了。徐玉知道這件事,邀約我的法國籍上司吃飯,向他大灌迷湯,極力推薦我的作品,他終於答應把作品送去總公司。這件事我是後來才知道的。可惜,總公司那方面一直石沉大海。
「怎麼樣?你的乳房算不算下垂?」我問她。
「幸虧沒有下垂,仍然很堅挺。」她滿意地說。
「大胸不是一件好事。」我嚇唬她:「重量太大,會比別的女人垂得快。」
「我認為導致女人乳房下垂的,不是重量,也不是地心引力。」徐玉說。
「那是什麼?」我問她。
「是男人那雙手。」徐玉咭咭地笑:「他們那雙手,就不能輕一點。」
「我想買一個新的胸罩。」徐玉咬著鉛筆說。
「你上星期不是剛買了一個新的嗎?」我問她。
「不要提了,前幾天曬胸罩時不小心掉到樓下的雨棚上,今天看到一隻大鳥拿來做巢。」
「那可能是全世界最昂貴的鳥巢。」我笑著說。
「那隻大鳥也許想不到在香港可以享受到一個法國出品的蕾絲鳥巢。」徐玉苦笑。
「你要一個什麼款式的?」我問徐玉。
「要一個令男人心跳加速的。」她挺起胸膛說。
「索性要一個令他心臟病發的吧!」我在架上拿了一個用白色彈性人造纖維和蕾絲製成的四分之三杯胸罩給她。四分之三杯能夠將四分之一乳房露出來,比全杯胸罩性感。我手上這款胸罩最特別的地方是兩個罩杯之間有一隻彩色的米老鼠,性感之中帶純情。
「很可愛。」徐玉拿著胸罩走入試衣間。
她穿上這個胸罩,胸部完美無瑕,兩個罩杯之間的米老鼠好像要窒息,我真埋怨我母親只賜我以三十四A而不是三十六A。
「糟糕!」她突然尖叫,「我忘了買雜誌。」
「哪一本雜誌?」
「《國家地理雜誌》。」
「你看這本雜誌的嗎?」
「是宇無過看的,糟了,書局都關門了。他寫小說有用的。」
宇無過是徐玉現在的男朋友,他在一間報館任職副刊編輯,同時是一位尚未成名的科幻小說作家。宇無過是他的筆名,他的真名好像也有一個宇字,可是我忘了。
「陪我去買雜誌。」徐玉著急地說。
「這麼晚,到哪裡找?」
「到哪裡可以買得到?」徐玉反過來問我。
「這個時候,中環的書局和書攤都關門了。」
「出去看看。」徐玉拉著我,「或許找到一間未關門的。」
「我要負責關店,你先去。新世界大廈橫巷有一個書報攤,你去看看,或許還有人。」
徐玉穿著三吋高跟鞋飛奔出去。
二十分鐘後,我到書報攤跟她會合,她懊惱地坐在石級上。
「收攤了。」她指著書攤上的木箱。
所有雜誌都鎖在兩個大木箱裡。
「明天再買吧。」
「雜誌今天出版,我答應過今天晚上帶回去給他的。」
徐玉突然抬頭望著我,向我使了一個眼色。
「你猜木箱裡會不會有那本雜誌?」
「你想偷?」我嚇了一跳。
「不是偷。」她開始蹲下來研究木箱上那一把簡陋的鎖。
「我拿了雜誌,把錢放在箱裡,是跟他買呀!」徐玉把皮包裡的東西倒出來,找到一把指甲刀,嘗試用指甲刀撬開木箱上的鎖。
「不要!」我阻止她。
我的心跳得很厲害,我不想因為偷竊一本《國家地理雜誌》而被關進牢裡。
徐玉花了很長時間,弄得滿頭大汗,還是無法把鎖解開。
「讓我試試。」我看不過眼。
「你們幹什麼?」一個穿著大廈管理員制服的男人在石級上向我們叱喝。
徐玉連忙收拾地上的東西,拉著我拚命逃跑,我們一直跑到皇后像廣場,看到沒有人追上來才夠膽停下來。
「你為了他,竟然甘心做賊,你還有什麼不肯為他做?」我喘著氣罵她。
徐玉望著天空說:「我什麼都可以為他做。我可以為他死。」
我大笑。
「你笑什麼?」
「很久沒有聽過這種話了,實在很感動。」我認真地說。
「我有一種感覺,宇無過是我最後一個男人。」
「你每次都有這種感覺。」
「這一次跟以前不同的。我和宇無過在一起兩年了,這是我最長的一段感情。我很仰慕他,他教了我很多東西。他好像是一個外星人,突然闖進我的世界,使我知道愛情和生命原來可以這樣的。」
我見過宇無過幾次,他長得挺英俊,身材瘦削,愛穿襯衫、牛仔褲、白襪和運動鞋。我對於超過三十歲,又不是職業運動員,卻時常穿著白襪和運動鞋的男人有點抗拒,他們像是拒絕長大的一群。宇無過的身形雖然並不高大,但在徐玉心中,他擁有一個很魁梧的背影。宇無過說話的時候,徐玉總是耐心傾聽。宇無過在她面前,是相當驕傲的。因此使我知道,一個男人的驕傲,來自女人對他的崇拜。
「去看電影好不好?」徐玉問我。
「這個星期上映的三級片我們都看過了。還有好看的嗎?」
「還有一部沒有看。」
看三級電影是我和徐玉的餘興節目之一,自從去年年初看過一部三級電影之後,我們經常結伴去看三級電影。三級電影是最成功的喜劇,任何喜劇都比不上它。那些健碩的男人和身材惹火的女人總是無緣無故地脫光衣服,又無緣無故地上床。我和徐玉常常在偌大的戲院裡捧腹大笑。
兩個女人一起去看三級電影,無可避免會引起其他入場觀眾的奇異目光,但這正是我們看電影的樂趣之一。男人帶著負擔入場,希望那部三級電影能提供官能刺激,可是女人看這種電影,心情不過像進入遊樂場內的鬼屋,尋求刺激而已。
從戲院出來,我跟徐玉分手,回到中環我獨居的家裡。
我跑上二樓,脫掉外衣和褲子,開了水龍頭,把胸罩脫下來,放在洗手盆裡洗。我沒有一回家便洗內衣的習慣,但這天晚上天氣燠熱,又跟徐玉在中環跑了幾千米,回家第一件事便想立即脫下胸罩把它洗乾淨。這個淡粉紅色的胸罩是我最喜歡的一個胸罩。我有很多胸罩,但我最愛穿這一個。這是一個記憶型胸罩,只要穿慣了,它習慣了某一個形狀,即使經過多次洗滌,依然不會變形。我不知道這個意念是不是來自汽車,有幾款名廠汽車都有座位記憶系統,駕駛者只要坐在司機位上,按一個掣,座位便會自動調節到他上次坐的位置。我認為記憶型胸罩實用得多。但記憶系統不是我偏愛這個胸罩的主要原因,我第一次跟阿森袒裎相見,便是穿這一款胸罩,他稱讚我的胸罩很漂亮。穿上這個胸罩,令我覺得自己是一個女人。
阿森今天晚上大概不會找我了。
清晨被樓下蛋糕店烤蛋糕的香味喚醒之前,我沒有好好睡過。今天的天色灰濛濛的,一直下著毛毛細雨,昨天晚上洗好的胸罩仍然沒有乾透,我穿了一個白色的胸罩和一襲白色的裙子,這種天氣,本來就不該穿白色,可是,我在衣櫃裡只能找到這條裙子,其他的衣服都是縐的。
走出大廈,森在等我。他穿著深藍色的西裝,白襯衫的衣領敞開了,領帶放在口袋裡,他昨天晚上當值。
「你為什麼會在這裡?」我故意不緊張他。
「我想來看看你。能不能和我一起吃早餐?」
「你不累嗎?」
「我習慣了。」
看到他熬了一個通宵的憔悴樣子,我不忍心拒絕。
「家裡有麵包。」我說。
我和森一起回家,然後打電話告訴珍妮我今天要遲到。
我放下皮包,穿上圍裙,在廚房弄火腿三明治。
森走進廚房,抱著我的腰。
「你知道我昨天晚上去了哪裡嗎?」我問森,我是故意刁難他。
森把臉貼著我的頭髮。
「你從來不知道我每天晚上去了哪裡。」我哽咽。
「我信任你。」森說。
「如果我昨天晚上死了,你要今天早上才知道。如果我昨天晚上跟另一個男人一起,你也不會知道。」
「你會嗎?」
「我希望我會。」我說。
如果不那麼執迷的只愛一個男人,我也許會快樂一點。愛是一個負擔。唐文森是一間大銀行的外匯部主管,我們一起四年。認識他的時候,我不知道他已經結婚。他比我年長十年,當時我想,他不可能還沒有結婚,可是,我依然跟他約會。
在他替我慶祝二十五歲生日的那天晚上,我終於開口問他:「你結了婚沒有?」
他凝望著我,神情痛苦。
我知道他是屬於另一個女人的。
做為第三者,我要比任何女人更相信愛情,如果世上沒有愛情,我不過是一個破壞別人家庭幸福的壞女人。
|
|